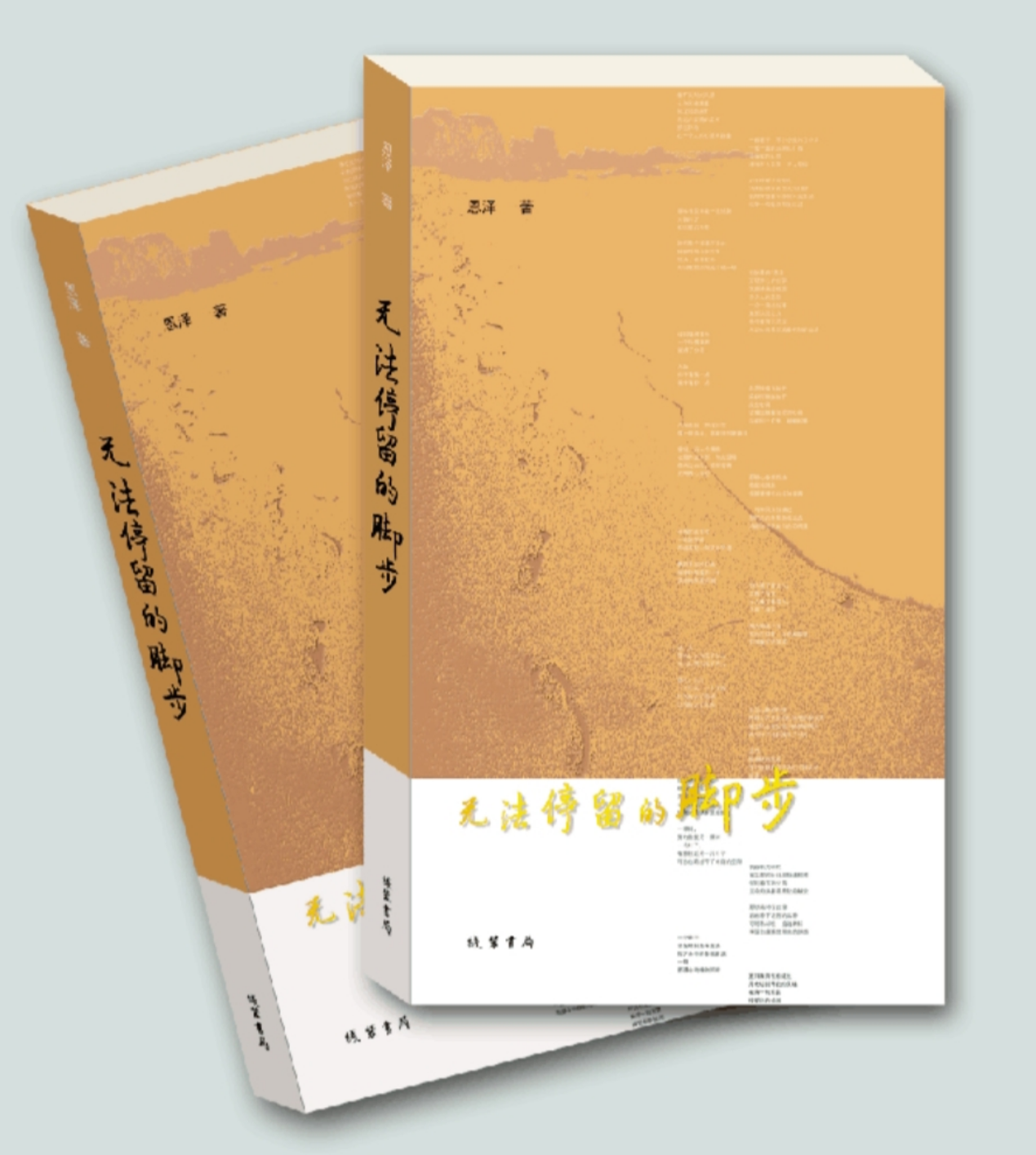
乡愁,细节刻画中的情感
——读恩泽的诗《父亲的村庄》
杨喜来
和恩泽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在他进入北京诗社微信群不久,就组织大家去妙峰山脚下的于家大院参观。并由此又结识了石景山作协的几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诗人。大概是去年五、六月吧,天气比较热。那天从地铁站一出来,就看见身材高大的恩泽手里攥瓶矿泉水在焦急地张望着。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他的形象已经在他创建的“大家传媒”微信平台多次
见到,所以并不陌生。很快,我们成了很熟悉的朋友,甚至是好兄弟。得知他出版了诗集,还有一些出乎意料,因为,他在北京诗社一直说自己刚刚写诗。不出半年就整出那么一本厚实的诗歌作品,让人感到他开始没有说实话。但是当你渐渐了解他以后,就会发现,他说的应该是真的,因为他非常勤奋。也许是多年军旅生活造就了他严谨及时的工作作风。诗社开展的很多活动,参加回来后,不管多晚,他一定及时做出宣传信息发布出来。有时候还要提前征求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在平台发布。正是基于这种印象,才相信诗集中这些作品,应该都是这一两年中写的。拿到恩泽的诗集,认真拜读,感到他编辑的很用心。诗集中分了很多单元,我最感兴趣的是“亲情”、“乡情”部分。在这两组作品中,我常常可以进入到他所描写的那个环境、那个氛围之中,再一次体会那一种深入骨髓的情感波澜。比如他写的《父亲的村庄》:
小时候村庄很大
父亲拿着藤条追打我
我总也跑不到头
现在的村庄很小,父亲在村头
咳嗽一声,我在村尾就听到了
当村庄逐渐长高
父亲的目光逐渐失落
他把爬犁擦得光亮
吝整整地挂在门前墙上
如如今成了他孙女好奇的玩具和自拍的道具
父亲的鸡鸭和猪被水泥路上的电动车小轿车撵來撵去
最终也挂到了墙上
挂到墙上的还有爷爷、姥姥、大伯、三叔他们好多人的照片
父亲一直希望我离开这个村庄,越远越好
父亲很自己把我生在了这个贫穷的乡村
我也曾挣扎着想方设法去闯荡外面的世界
却发现魂牵梦萦的,仍然是父亲的老村庄
村庄变成了城市
熟悉的学校、牛棚和枣树消失了
父亲一直想让我回去
可我已无法返回
一些陌生的新面孔
他们看我和我看他们的眼神一样冷漠
我把村庄丢了
村庄把我父亲丢了
他们看我和我看他们的眼神一样冷漠
我把村庄丢了
村庄把我父亲丢了
我到许多村庄去找父亲
只有一个村庄里有他的身影
这个村庄在诗人恩泽的眼睛里(也不只是眼睛的视觉范围,还包括耳朵的听觉范围,
内心的感触记忆范围)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化是用很形象的细节来表述的:“小时候村庄很大/父亲拿着藤条追打我/我总也跑不到头/现在的村庄很小,父亲在村头/咳嗽一声,我在村尾就听到了”村庄的变化是因为自己的“小时候”与“现在”这个年纪上的变化,还是自己身材的变化?还是村庄自身的变化?这一切,却又体现出父亲的变化:小时候父亲是可以追打一个顽皮的孩童的,现在却已经用“咳嗽”来概括今天了。而且,这声咳嗽在村尾都可以听见。是小村小了,还是咳嗽声音太大了?多重复杂的因素都凝聚在这短短的几行诗句里,使诗歌具有了极大的张力,可以漫延出很多枝节,可以延伸很远。 然后写“他把爬犁擦得光亮/齐整整地挂在门前墙上/如今成了他孙女好奇的玩具和自拍的道具”爬犁是什么?可能有人会说就是一件农具而已,其实对于ー个真正的农民来说,农具,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臂膀、如手足。他的所有作为农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体现,完全依赖于那么简单的几件农具,相当于作家手中的笔,武士手中的刀。正是这种情感因素在里面,所以即便这些农具不用了(也许是暂时不用),也要擦得光亮,在门前挂好。这是一个纯正农民的表现,是我国农业社会里乡村农民的经典动作。让我想起了柳青的《创业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们的作品里没有这个细节,但是我却想起了这些作品,因为这些作品都同样是刻画了中国农民。同时,我也想到了我的家乡,想到了我的父亲和乡亲们,在秋收以后,他们就是这样对待家里那些心爱的农具的。 让人产生震撼的是,一个极为强烈的对比出现了——父亲珍爱的农具到了他孙女这一代人眼里,成了玩具,成为孙女自拍的道具。“咔嚓”一声,一个小女孩儿摆出可爱的pose。这种阳光鲜亮的形象重叠在一个数干年农业社会象征的爬犁上,是一种巨大的反差,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村庄的变化,是父亲生活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过程中,诗人的感情是复杂的。欣慰,惆怅,失落在心里不断交替。 首先,“父亲一直希望我离开这个村庄,越远越好/父亲恨自己把我生在了这个贫穷的乡村/我也曾挣扎着想方设法去闯荡外面的世界”这是每一个父亲的想法,都不愿自己的后代依然像自己一样生活,自己吃过的苦,都不愿孩子去品尝,这是天下父母一样的心思。其次,作为后代,也不会甘心情愿重复父辈的生活,更愿意去闯荡自己的一片天地。那么当这一切都随时间流逝之后,一个在外面闯荡成功的成年人本该是踌躇满志、志得意满,但是涌上心头的却是一种淡淡的苦涩,“村庄变成了城市/熟悉的学校、牛棚和枣树消失了/父亲一直想让我回去/可我已无法返回”是的,一个正值扎根的树苗被移植到他乡,那么它就是那里的绿荫,就是那里的一棵树。像蒲公英的种子,在一柄小伞的带领下它飄走了,那么它无法回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的种子,我们都会在梦的引领下走到远方,然后在回忆故乡的感情里,在远方扎根。诗人对家乡的怀念,是他已经找不到那个他熟悉的家乡了。寻找故乡,应该是每个人诗歌的主题,也是生存的主题。
杨喜来,笔名杨喜莱,北京大兴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青少年诗词创作协会理事。出版有散文集《年轻的海》、《行走的人生》,发表中篇小说《寂寞的龙河湾》、《祖父的影子》等作品。
-
2025-11-22
-
2025-11-21
-
2025-11-19
-
2025-11-18
-
2025-11-16
-
2025-11-12
-
2025-11-08
-
2025-11-08
-
2025-11-05
-
2025-11-03
-
2025-11-03
-
2025-11-02
-
2025-11-01
-
2025-11-01
-
2025-11-01
版权所有:旅游文化网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清路22号 投稿及违规不良信息举报邮箱:zgzhoubu@126.com
免责声名:部分内容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或其它问题与本网联系我们会尽快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