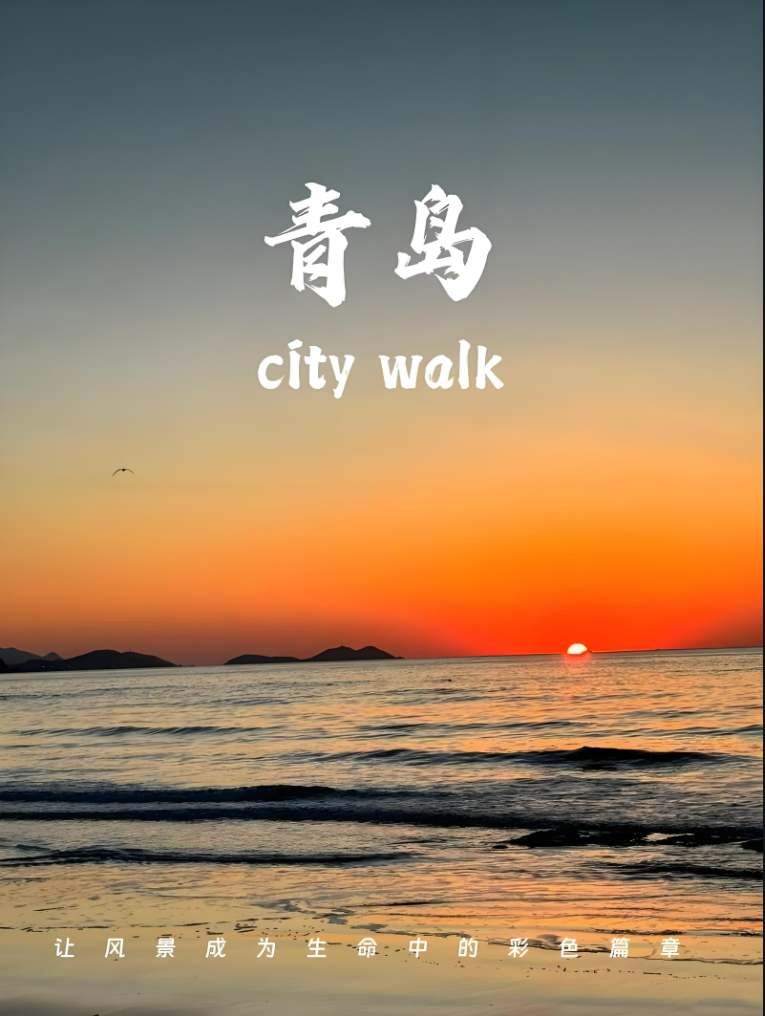
不期而遇这片海
作者 北塔
昨晚有月全食,在回京的路上,我边开车,边欣赏,不由自主回想起最近一次在青岛亲近月亮的情景。
六月下旬,我曾回琴岛避暑,此番文友们安排的活动比较多,而且我要提前离开,去湖北参加诗会——明知炉有火,偏向火炉行。所以,我基本没有安排出游,尤其没有去野游。
诗友、导演、朗诵家高云华先生从媒体上得知我来岛城的消息,立即热情地要为我践行。傍晚时分,他和摄影家王菁女士一同开车到金沙滩接上我和小女顺子之后,说要带我去一个新去处。我问什么去处。他说,他也不太清楚,是朋友推荐的,他也是第一次去;听说是一个新开发的或者说尚未开发完善的郊野所在。我立即心仪,我偏爱不太完善的人和物,景点尤其如此,有野趣者哉。连云华先生和王菁女士两位本地文旅界的闻人都没去过的地方,肯定野趣十足。
车子迎着温暖的晚霞,乘着凉爽的晚风,向着郊外的郊外行驶,一道道缓坡,一条条弯路,穿过一片片小树林,拐过一块块青草地。我虽然从十几年前开始,就成为半个黄岛人,却很少在岛上游蹿,所以处处感到陌生、新鲜。车子跟着导航,在一片果树林里转了两个弯后,来到海边。

我下车抬头一看,是一扇门——一个门框,没有墙的门。墙是用来堵的,堵住人的出入,所以其量词就是“堵”;而门是用来通的,尤其是这没有墙的门,永远开着。门框旁边矗立着一根木头,上面钉着白、红、蓝等不同底色的五块小牌子。上面的文字,无论是中文还是外文,都用的是精巧的美术字体。最上面那块写的是“相约这片海”。其下面那块写的是“走下去,就是海边”。我意识到:虽然眼前就是大海,但脚下是一块离海面有好几米的台地,所以,需要往下走,才能达到真正的海边,或者说紧海边,能够对海“动手动脚”的滩涂。
我环顾四周,我们所在的台地上只有极少量简易房,绝大多数是帐篷,少则几顶一处,多则十几顶一处,全都面向大海敞开着口子;这就是一间间包房,方便食客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欣赏美景。这比五星级宾馆的美食多了一道美味。我们赶紧把所带的什物放进其中的一个,主要是云华带来的他私藏的美酒。

云华也是摄影师,而且颇为专业,长枪短跑都随身携带,而且还有三脚架。去年腊月,我跟他一起在新疆阿勒泰采风,即便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林海雪原,即便穿着铠甲一般的厚重外套,他也时常带着这些庞然大物,拍摄雪都的绝美雪景,包括给我拍了多张留影。他知道我们迫不及待要跟大海亲近,就让我们先去海边,他自己则专心拍摄。
我往下走了几步,就到了平坦的新铺的木栈道上,回头一看,坡上有一块更加有意思的牌子,是用帆布做的,上面写着两个大大的粗野的毛笔字:“去野”。我想,这“野”字应该是动词,大概的意思是“撒野”或“撒欢”,撕破斯文或假装的斯文,过一下哪怕是有点生猛的生活,盛产生猛海鲜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的“野”地。我还想,这两个字倒过来读也通,即“野去”。那么,这个“野”字就变成了副词,意思大概是“不那么正经地”或“不那么假正经地”。两个月后,我应邀到塞北去采风,有一位同行文友开的越野车的后面出现同样字体的“去野”。另一个同行文友告诉我,这其实是一个户外运动的品牌名。我恍然明白,“户外”者“野外”也。我们在户内过的是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户外,就可以有点“野”,甚至“越轨”。这大概是户外运动的真谛和魅力所在吧。
我向着大海走去,到了海滩,才从路标上得知,这里其实还是个渔村,叫做鱼鸣嘴。这个名字也取得让我敬服。嘴大概指的是这里有个小渔港,形似大海伸入陆地的嘴,当然也可以想象为陆地迎纳大海的嘴。全世界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这样的陆海接吻的地貌命名为“嘴巴”,所谓“入海口”之“口”不就是“嘴巴”吗?
沿途遇到许多“臭名昭著”的浒苔,横七竖八铺排着。乍一闻,没什么腥臭味;乍一看,碧绿碧绿的,还有点可爱;但它们裹挟鱼虾、侵占海滩的样子,类似于外来侵略者裹挟汉奸伪军侵占我们的固有生存空间,委实可恶。有重型铲车来回作业,把它们一摊摊收拾起来。据说,它们不会被焚烧或填埋,而是会被制作成有机肥,这算是它们最好的结局——有利于人类。无论是多么野蛮的有害的东西,人类总能想方设法变废为宝、变害为利。
这处海滩,没有沙滩,只有乱石,或黑乎乎,或黄乎乎,嶙峋的、倒错的、张牙舞爪的、面目狰狞的。我平生酷爱石头,无论美丑,无论正奇,无论棱角分明还是圆润平滑。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石头散列在海滩上,似乎是我们走向大海的障碍;但只要我们大胆而小心地慢慢走,还是能穿过它们的夹缝,或踩着它们的头顶,克服这些貌似死硬的障碍。很多人,男女老少,尤其是小孩,都选择停下来,在石头和石头之间,尤其是石头缝里,但凡有水洼的地方,翻来倒去,寻找寄居蟹或小虾米或小蜗牛,哪怕翻找半个小时,只收获一枚指甲般的寄居蟹,也不亦乐乎,甚至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我听到不少外地口音,山西的,湖南的,甚至西部省份的,大抵从内地难得来趟沿海的人们,这样的兴致更高。
我鲜有沿途寻虾摸蟹的小确幸,所以干脆以不规则的步伐,踏过石头门的秃顶,直奔大海。我终于站到了一块只在滔滔白浪中冒出头顶的礁石上。浪头像蟒蛇的舌头,时不时舔过我的脚板,还好没有窜上来咬住我的脚踝乃至膝盖。我凝望着它们,把它们的汹汹来势当做嬉戏,把它们的咻咻乱叫当做吟唱,把它们的上下翻飞当做曼舞;哦,我不是来寻仇的,也不是来找食的,而是来审美的。我沉浸于大海慷慨赋予我的美感,不知夜之将至。
这时,云华兄来电催促我们赶紧回到台地上去,因为夕阳西下,光线渐渐变暗,拍照效果将大打折扣,而他还要带着我一起朗诵我的诗并制作专题视频呢。

等我紧赶慢赶,赶回台地。云华兄已经等得颇为心焦。他让我站在门框里,试了一下镜头。毫无疑问,那是拍海景的最佳位置;我们一试,就定了,然后开始选诗。一开始,云华想让我读一首中英文双语的,我在手机里找到一首写草原的,但主题是蒙古刀,充满杀机和杀气,他认为不适合这般良辰美景。我说,那就来一首我前年乘坐“神曲”号邮轮在地中海深夜深处写的月亮诗吧,题为《海上落明月》。他连声说好,因为这时,我们发现,月亮已经缓缓揭开自己的云纱,脉脉含羞地露出半个脸蛋;待我们仰观时,她又盖上,然后又掀开。周边的华灯也亮了,是真正的华灯,五颜六色,光彩悦目。太阳也还没退场,晚霞尤其绚烂。因此,那时,日、月、灯三光同辉,这提高了我们读诗的兴致。于是,在月亮的青睐和倾听下,我们俩联合读了我这首献给“大月”的诗。等我们彻底读完——云华兄作为精益求精的导演和艺术家,让我跟他合诵了三遍,直到吐字、手势和姿态以及光影各方面都让他满意为止——太阳才披着晚霞悻悻而知趣地离去。或许太阳知道,我们感情的天平已经彻底偏向太阴——尽管她是那样面目模糊、态度不清。
我喜欢并怀念鱼鸣嘴的那片海,那里的游人、汽艇和直升机都还只是乱石之间、骇浪之间和乱云之间的点缀,那是一片还能听到鱼鸣的海,那是一片让我怀念地中海的大月的海,那是一片让我在任何地方看到月亮都会忆起的海。

作者简介
北塔,生于姑苏,现居大都,诗人、学者、翻译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原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曾受邀赴美国等近50国参加各类文学、学术活动,包括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等,曾率中国诗歌代表团出访秘鲁等约30国。有作品曾被译成罗马尼亚文等近20种外文,曾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已出版诗集《滚石有苔》等各类著译约30种。有“石头诗人”之称。
-
2026-02-01
-
2026-02-01
-
2026-01-27
-
2026-01-27
-
2026-01-26
-
2026-01-26
-
2026-01-25
-
2026-01-23
-
2026-01-23
-
2026-01-23
-
2026-01-22
-
2026-01-21
-
2026-01-21
-
2026-01-18
-
2026-01-17

版权所有:旅游文化网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清路22号 投稿及违规不良信息举报邮箱:zgzhoubu@126.com
免责声名:部分内容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 如因作品内容或其它问题与本网联系我们会尽快处理。




